四、结束语——共助体系的形成
垃圾问题,如作为后现代社会的日本那样,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得以解决。但更让人忧虑的是对现代化毫无防备的、彻底的拥抱。当这样一个现代化的病理,与中国农村社会正在经历的社会病理相结合的时候,垃圾就不再只是一个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的课题。可以说,农村生活垃圾是多重病理相叠加而凸显出来的问题,对其诊断和治疗也应该思考一副综合性的处方。因此,本文分别从三个角度,即行政体系的公助、村民主体间的互助和对村民自助的学习触发,探讨了根植于村落空间再造的治理模式。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那么,其顺序应该是,自助、互助、公助,也就是说在自助和互助不能完全应对的时候,才会有公助登台亮相的机会。但在中国农村地区,无论是快速清除共有地散乱的垃圾,还是公共领域成立和对乡土教育的推动,公助的力量不可或缺。但长期对公助的依赖,不啻于强化了村民生活世界的空洞化和殖民化,再加上无论是乡村干部或是普通村民对社会发展的概念和规划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甚至将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其问题的所在也折射出当今社会整体对后者轻视的现状,因此本文特别强调了二者的区别,这是因为对于同时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质的生活垃圾问题,社会发展对互助和自助的促进更是长久的、根本性的机制。而在现阶段,对中国农村生活垃圾的现实处方是,从这三个层面同时推进,以形成有机的共助体系,才能使4R的理念与实践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原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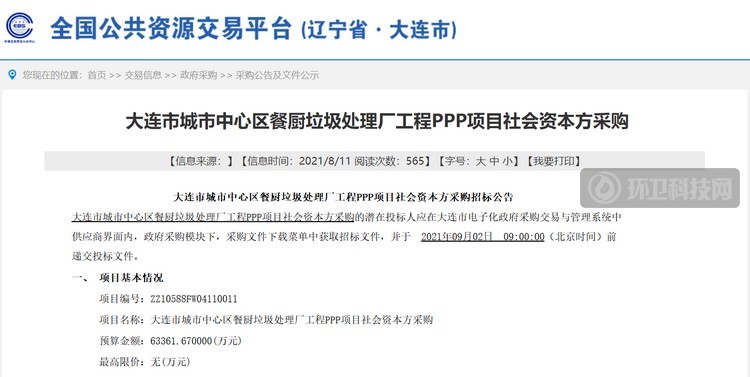





 盈峰环境排水抢险车赴
盈峰环境排水抢险车赴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