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的转变与环境问题的相关性同样体现在J省D县的农村里。D县的J村不仅面临着生活垃圾增多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养殖业的兴起,禽类和牛、猪等家畜的排泄物在当地引起了一系列的难题。村民的养殖场大多设置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招致大量的苍蝇,异味也不断引起邻里之间的纠纷。未经任何处理的排泄物被放置在道路和田端,成为寄生虫的温床,雨天过后,排泄物被冲进田里,引起农作物的枯死。现代科学诞生之前,世间没有无用、可丢弃之物。动物的排泄物本来作为肥料,化为土地的养分,滋养农作物,即人类•动物的排泄物→农作物•土地→食粮→人•动物,这一循环体系在农村社会里的劳作与生计发挥着功能。然而,传统的循环哲学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不堪一击。
D县位于省会城市的2小时经济圈内,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外出务工的村民逐渐增多。在所调查的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或长或短的外出务工成员。当中,所访问的老年人都坚持认为,不会让自己的孩子留在农村,但自己不想去城市生活,觉得不会适应那里。J村C村民夫妇(丈夫62岁,妻子59岁)都表示,“去城里生活过,但还是觉得这里(农村)好,城市什么都贵,不像这里还能种点菜和水果,冬天在窖子放些蔬菜,不用再买了。”该夫妇的儿子、D村民(男,36岁)则表示,“家里除了苞米地以外,自己(没时间)已经不种菜了,苞米价格又低,自己和老婆都要出去打工,而且为了孩子的将来考虑,还是想让他在城市工作、生活”。两代村民相较而言,父母在自家院子里种菜、种水果可以节省一部分开支,而儿子除了苞米地的收入以外,要寻求打工才能拟补家用。这就意味着,原本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村落共同体的自给自足或互帮互助的体系得以维持,当生计被纳入大城市经济圈后,加大了对货币经济的依赖。因此,进城打工并没有实现他们最初的预想——能够使自己的生活比父辈更加宽裕一些,相反在城里的打工经历使他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穷困感和焦虑。
然而,维持生计方式的转变,除了没有让他们更加宽裕之外,却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加重了环境的恶化。C村民(妻子)说,“儿子只在农忙期回来帮助种地,其余时间都在外面打工挣钱……粪便我们都不用了,就用化肥,省事还干净。”E村民(女,42岁)说,“家里也没几亩地,丈夫在外面打工,我也有时候去(打零工),家畜的粪便早就不用了。”J村委会G干部说,“化肥的用量用法我们也都讲过,但是都图省事,本来化肥要分几次撒,但要去打工,没时间回来,所以干脆在种的时候,把(几次量的)化肥一起埋进去。”为了弥补与城市生活上的差距,村民不得不做出了一些作为个人的合理化决定,然而这种个体合理化的行为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使社会整体陷入不合理的状态。J省所在地被称为肥沃的黑土地,但黑土层已由开垦初期的80~100厘米下降到20~30厘米,每年流失的黑土层厚度为1厘米左右,同时有机质以平均每年0.1%的速度下降,导致土壤生物学特征退化,作物病虫害发生率提高,耕种全部依靠化肥来支撑。正如村干部E所说的那样,“土地本来是具有力量的,即‘地力’,可以自我消化、净化,但现在不行了,化肥已经让土地失去了这样的能力,村民觉得产量下降,于是就加大化肥的使用量。化肥是省事的、干净的,而动物的排泄物则是污秽的、麻烦的,以及没有人想让自己的孩子留在农村,这种对城市生活的向往,都可以看出村民对现代化毫无防备的拥抱。在这当中,与生态系统融合为一体的传统生活体系,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抛弃掉,甚至形成了化肥→土地退化→低产→加大化肥使用量→土地更退化的恶性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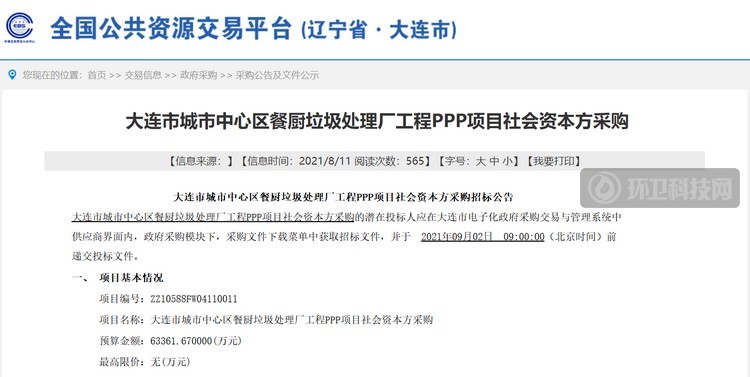





 盈峰环境排水抢险车赴
盈峰环境排水抢险车赴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